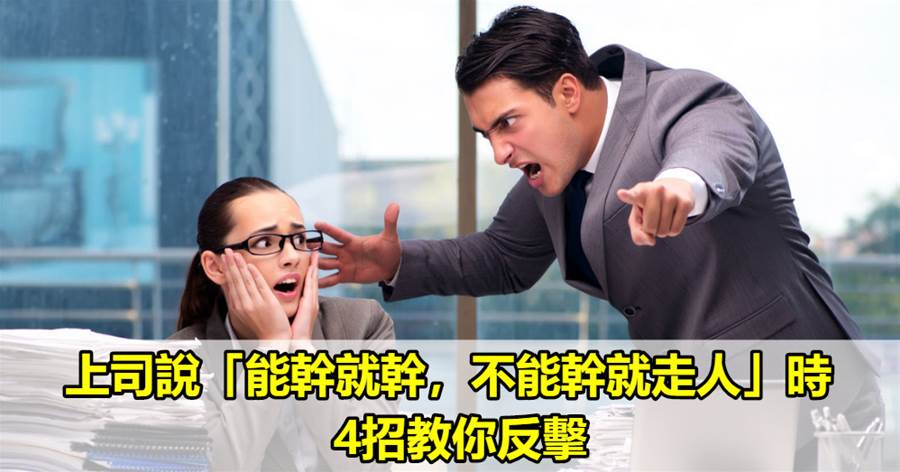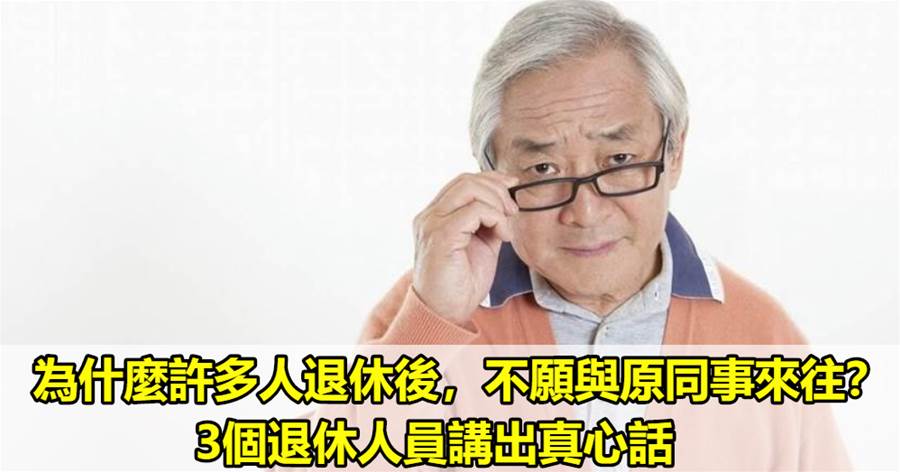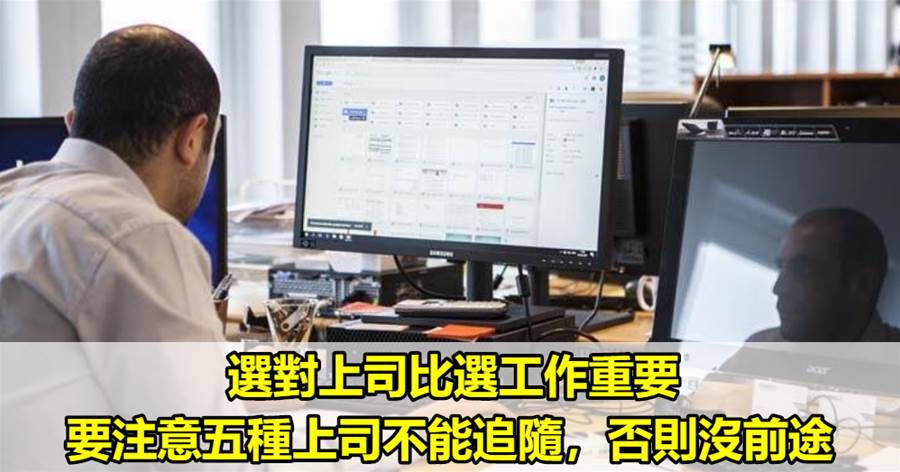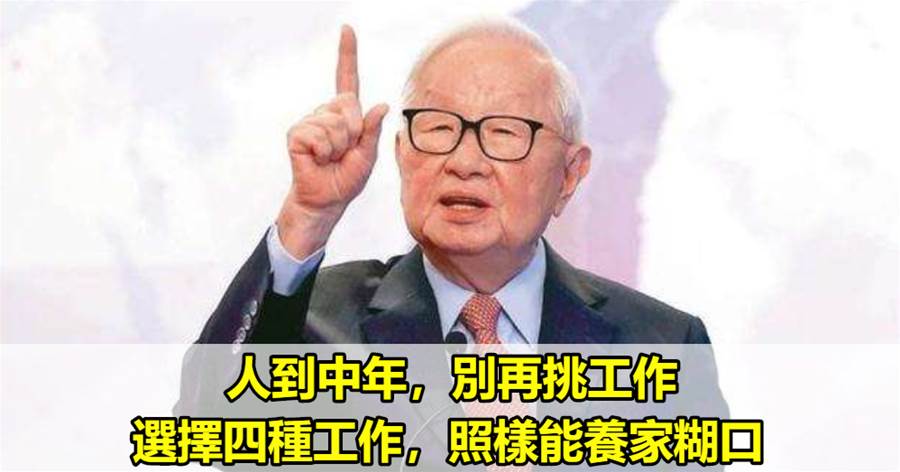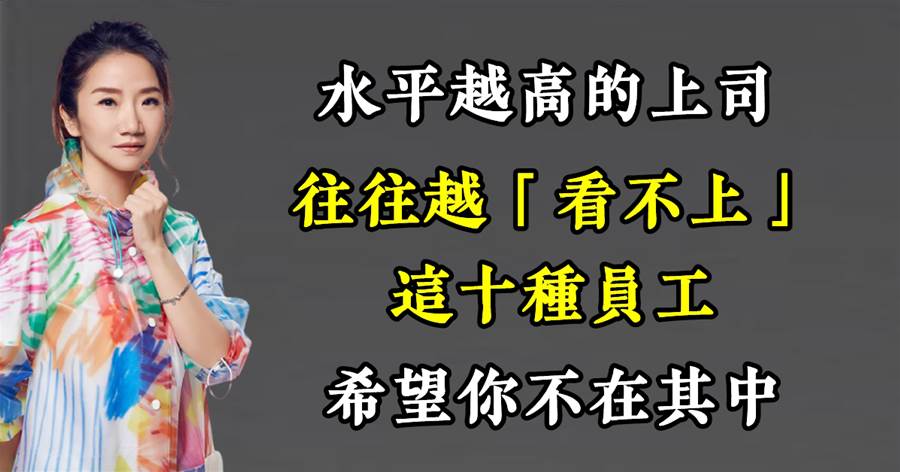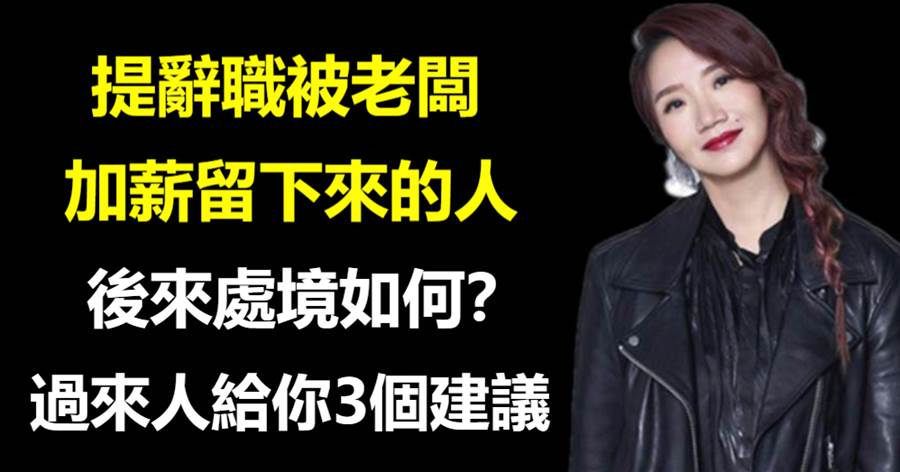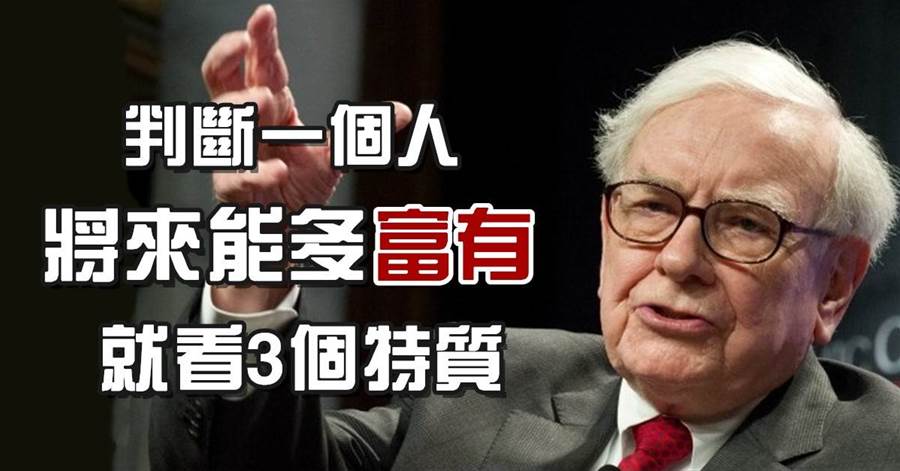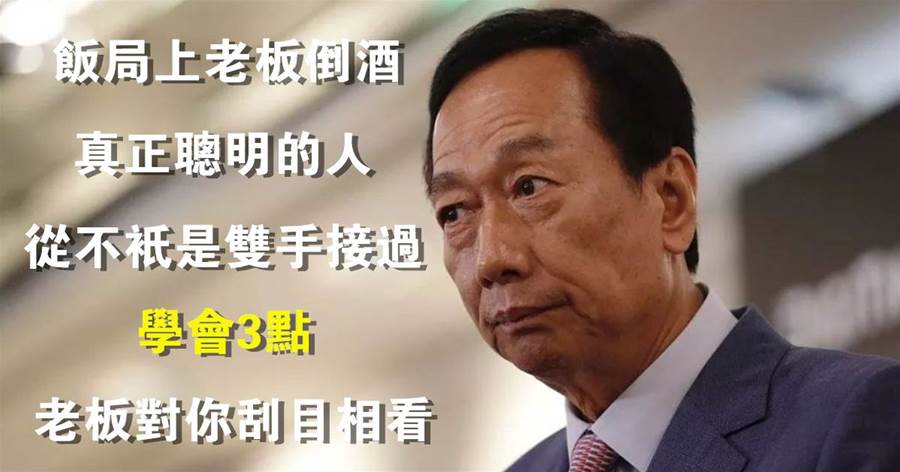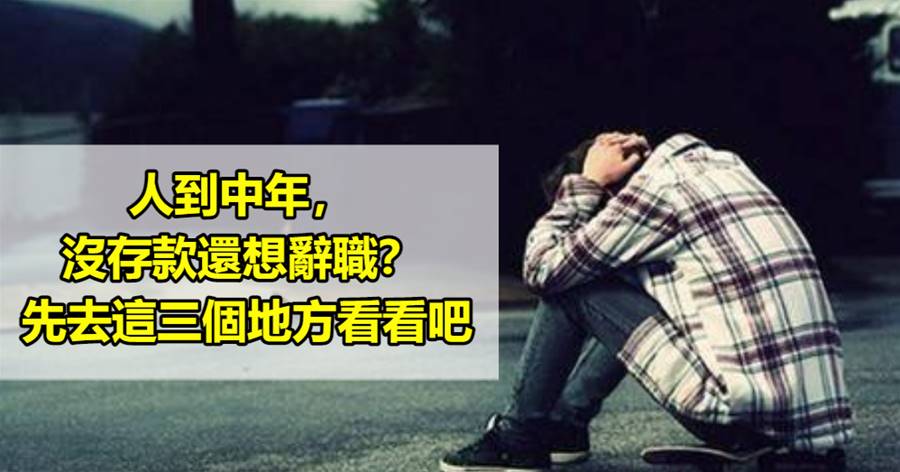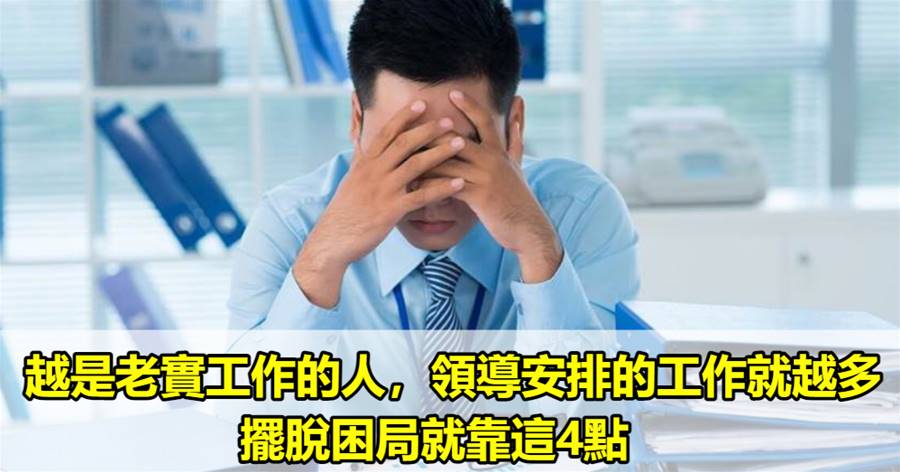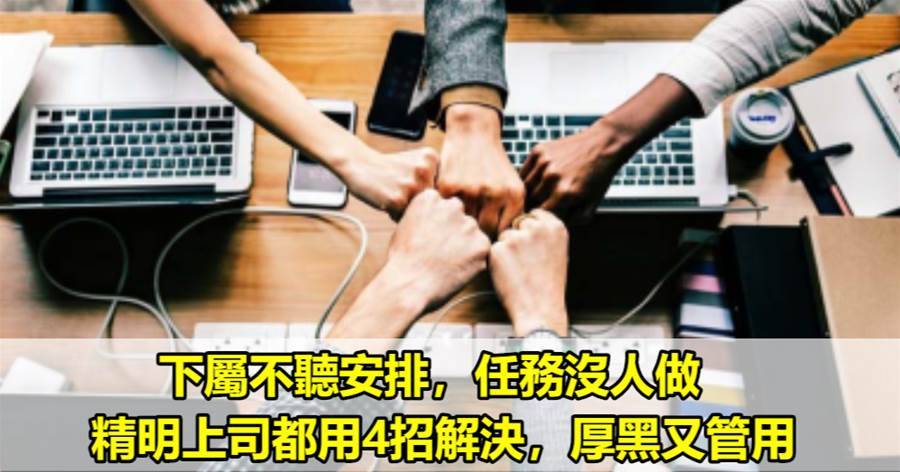唐文宗大和七年,杜牧奉命去揚州公幹。
在經過金陵地界時,他偶然遇見一位窮困潦倒的老嫗。
老嫗身著一襲白娟寒衣,頭髮糙枯如黃草,乾瘦的手臂青筋外露,眼底眉梢都刻滿了溝壑般的皺紋。
此情此景,令杜牧唏噓不已,腦海中浮現出十多年前那「如玉般的美人」:
京江水清滑,生女白如脂。
其間杜秋者,不勞朱粉施。
原來,這位老嫗不是別人,正是歷經四朝、被後人譽為「十大名妓」之一的傾城美人——杜秋娘。
她絕色無雙,15歲紅成頭牌,被兩朝帝王垂涎;
她才情俱佳,題詞一曲《金縷衣》成千古絕唱;
她清醒睿智,被唐憲宗奉為知己,享數年獨寵。
可儘管榮耀至此,卻還是在歷經半生浮沉起落後,因一時之錯,一切歸零,落得個無人可依的淒涼下場。
或許正如托・霍布斯所說:
「人每違背一次理智,就會受到理智的一次懲罰。」
看來,人生一世,想要好命到底,唯有時刻清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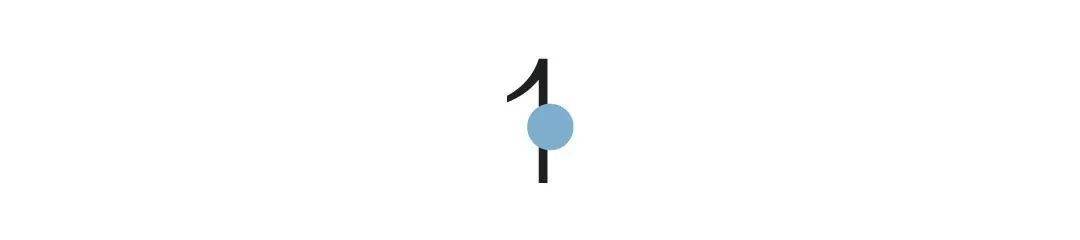
從名妓到寵妃:
女人頂級的智慧,是看清自己
秋娘命苦,三四歲的時候,父母便因戰亂早亡。
好心的鄰居把她接過去撫養,卻又因不堪天災兵禍,在秋娘8歲時,把她變賣給了當地最紅火的煙花之地——「藏嬌樓」。
藏嬌樓的頭牌金牡丹,一見秋娘就歡喜得不得了,她囑咐鴇母,定要好好栽培這個美人坯子。
從那天起,秋娘就開始一心學藝。琴棋書畫,舞蹈茶道,更在閑來之時自學詩詞,譜曲編舞。
靠著美色和才情,短短5年內,就成了遠近聞名的「小頭牌」,遠勝其他庸脂俗粉。

15歲那年,鎮海節度使李錡,在聽聞秋娘美名後,花重金買通了金牡丹的門路,把她招入李府,充任歌姬。
可早已名聲鵲起的秋娘,哪還甘願當個下等歌姬?
她心中清楚,李錡和那些秦樓楚館的客人一樣,雖然都喜歡看歌舞,卻又早已厭倦了傳統的舞曲形式。
而自己一向擅長以詩詞娛情,與尋常的歌舞姬相比要風雅不少。若能用心編排一曲,在關鍵時刻展露,必能獲得李錡青睞。
果然,數月後的一天,李錡遍邀賓客,來家中喝酒賞舞。
誰知剛一曲舞罷,就有人駁面子地說:「這都是去年時興的歌舞段子了,乏味得很。」
正當李錡面露尷尬,不知如何回復的時候,秋娘緩緩出場,輕歌曼舞間,徐徐吟出一曲自己題詞的小令《金縷衣》:
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惜取少年時。
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
短短四句,把秋娘的風韻情致展露無遺,惹得賓客掌聲雷動。詞中「人生苦短須盡歡」的意味,更是瞬間擊中年過半百的李錡。
他當晚就納了秋娘為侍妾,秋娘也因此登上了人生中第一個由自己主宰的臺階。
或許正如《呂氏春秋》所雲:「欲知人者,必先自知。」
一個人能自知,才能自渡。
世事難關皆是枷鎖,唯有看清自己,才是通關的第一把鑰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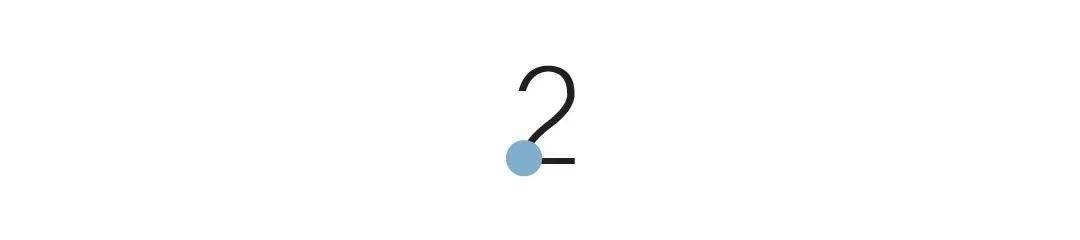
從紅顏到知己:
婚姻幸福的前提,是看清伴侶
「年少追夢,幾許閒愁,幾許閒愁,幾許躊躇。」
秋娘和李錡恩愛的日子沒過多久,李錡就因擁兵造反,被繼承皇位的唐憲宗李純,生擒腰斬。
而秋娘也只能被罰入皇宮的掖庭,成為最低等的奴婢。
有一天,秋娘做完灑掃的活計,獨自倚在亭子欄杆,看著四月裡的杏花疏影,滿枝蜂蝶,一時之間,回憶湧上心頭。
她慢慢站起身,再次輕聲唱起那曲《金縷衣》,腦中浮現的,是和李錡的恩愛往昔,和如今只能為奴為婢的境地……

她唱得淒美動人,歌聲在悠揚婉轉之上,更平添了幾分愁思,舞姿也變得更加羞媚纏綿。
這時,從遠處的樹影裡突然鑽出一人,一邊大聲鼓掌叫好,一邊目光熠熠地朝秋娘大步走來。
那人,正是唐憲宗李純。
一曲《金縷衣》,讓秋娘成了李錡的侍妾,更讓她搖身一變,從卑微的奴婢,化身成當朝唐憲宗的「秋妃」。
秋娘心中始終有一個警醒:自己如今的枕邊人,是君威不可冒犯的帝王。
他不可以被挑釁、被怠慢,身邊更不缺獻媚討好的女子。如果想要恩寵長久,就必須要將身份從千篇一律的妃子,變成無可替代的知己。
秋娘開始留心觀察,發現唐憲宗對那些諂媚奉承的妃子,總是淡淡的。
她就反向而行,絕不說太多巧取聖心的場面話,儘量讓自己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都自然流露。
這反倒讓唐憲宗覺得,此人不俗,願意和她掏心窩地說點體己話。
僅是如此還不夠,秋娘還發現,因為唐憲宗大力改革,時常遭到群臣反對,很多積弊朝綱的禍患都久久無法解決。

唐憲宗也因此總會把自己鎖在屋裡:有大臣進諫,他不願聽;有妃子獻媚,他懶得理。
唯有秋娘,細數了文景之治、始皇一統等多個古代帝王的例子,讓唐憲宗在潛移默化間,學會了更為折中的懷柔政策。
邊地矛盾因此得到緩解,唐憲宗的鐵腕心腸,也被秋娘剛柔並濟的手段,一次次化解。
數載過去,天下安定。宰相對唐憲宗說:「該多選些名家美女,充實後宮了。」
誰料唐憲宗一笑,說道:
「李元膺有‘十憶詩’,曆述佳人的行、坐、飲、歌、書、博、顰、笑、眠、妝之美態,今在秋妃身上一一可見,我還有何所求?」
從最初以美色入懷,到後來成為獨寵多年的秋妃,秋娘早已成為唐憲宗身邊,最不可替代的女人。
春天,他們臨湖觀魚,同放鴛鴦狀風箏;
夏天,同在簷下乘涼,調教白鸚鵡學舌;
秋天,乘風泛太液池,遙看牛郎織女星;
冬天,就著大雪紛飛,喝杯香茗吃烤肉。
秋娘順著唐憲宗的心思,既給了他尋常夫妻般的自在,又給了他帝王孤獨下的陪伴、軍師知己般的謀劃。

她看透了他,也因此成就了他。
正如網上的一句話:「下等婚姻互為人質,中等婚姻互相遷就,上等婚姻互相成就。」
相比自我感動地無窮付出,知己知彼的婚姻,才更能幸福長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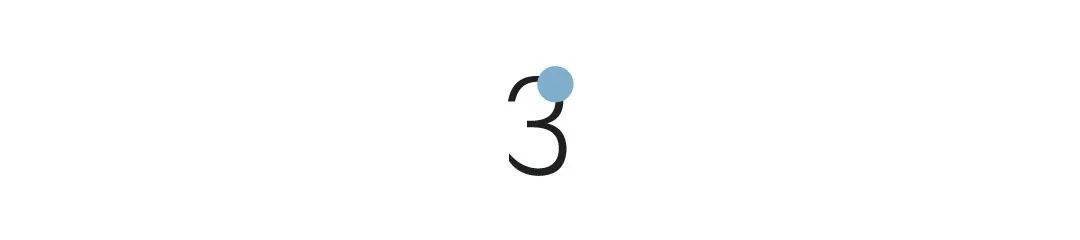
從皇族到庶民:
改寫命運的關鍵,是看清時局
「花謝花開緣底事?新梅重綻最高枝。」
秋娘曾重新題詞《金縷衣》,可惜,在和唐憲宗共用十餘年繁華之後,她卻再沒能綻放成「最高枝」。
元和十五年,唐憲宗李純暴斃。
繼位的李湛、李恒兩位天子相繼被殺,唯一還能堪當大任的,只剩一個被秋娘撫養長大的李湊。
只是那時,宦官專權,秋娘實在害怕自己和李湊會被宦官密謀殺害。
她終日惶恐,一邊苟且求生,一邊又因眼見三朝天子被害,心中塞滿了仇恨,漸漸燃起為唐憲宗復仇的奪位之心。
可她忘了,自己無兵無權,雖然身側有幾位能夠商討的大臣,卻並不佔優勢。
而對手有足以謀害三朝天子的威勢,他們早就安排了眼線,把秋娘的謀劃盡收眼底。

果然,還沒等秋娘與李湊奮起爭權,對手就以莫須有的理由,將他們趕出了皇城。
李湊被貶為庶人,秋娘被削籍為民,放歸故鄉。
返鄉的那天,秋娘回頭望向那座困了自己半輩子的皇城,北風像刀子一般紮在臉上,像是在笑話她,終究為一時糊塗買了單。
克制了半生,清醒了半生,到頭來又能如何?
只這一刹的誤判時局,就足以讓她脫去嬪妃服制,轉瞬成空。
放歸潤州的秋娘,無親無戚,無兒無女,只能住在道觀中,靠官府供養。
她白天要幹活農作,到了晚上想給自己縫製一身簡薄的單衣,還因為太窮,只能向鄰居借織布機。
數年之後,戰亂再起。無依無靠的秋娘,只能沿街奔逃,逃到一汪湖邊時,又累又冷。
她仰頭看著鵝毛般的大雪,耳邊再次響起《金縷衣》的調子。
這一生,她就像那朵開在枝頭最豔的花一樣:
因為適時,所以得到李錡青眼;
因為怡人,所以重獲李純寵愛。
可最後,還是因為一陣沒有預判的狂風驟雨,改寫了自己掙紮得來的美好結局。

天色漸漸暗下來,身邊逃亡的人都行色匆匆。
無人知曉,這個凍死在湖邊的窮酸老嫗,竟是一個傳奇了幾代的絕色佳人。
花,最終還是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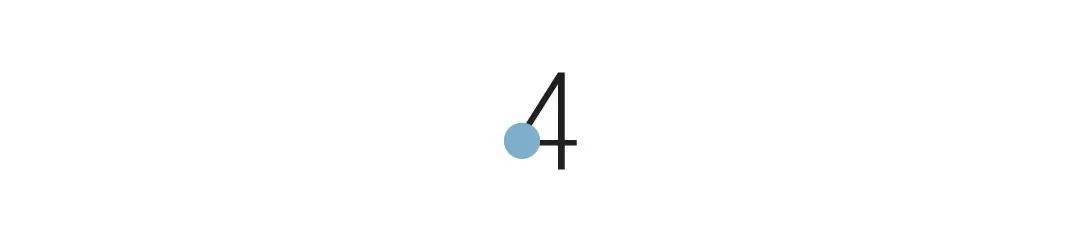
畢淑敏說:「歲月送給我苦難,也隨贈我清醒與冷靜。」
杜秋娘的一生,榮耀數十年,荒涼數十年,也皆因「清醒」二字。
豆蔻之年,她看清自己,借助不可替代的才情優勢,脫身風塵;
花信歲月,她看清伴侶,用滿腔溫柔給足陪伴,成全了多年良緣;
半老之際,她誤判時局,終究毀了自己辛苦攢下的半生福氣,可悲可歎……
原來人這一生,看清一時,未必得意;看清一世,才能贏到終局。
越知悉,越清醒;越清醒,越好命。
與大家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