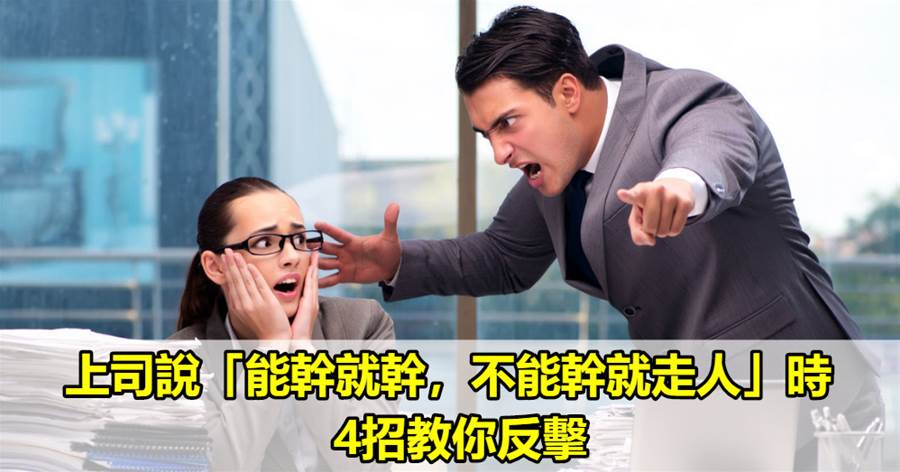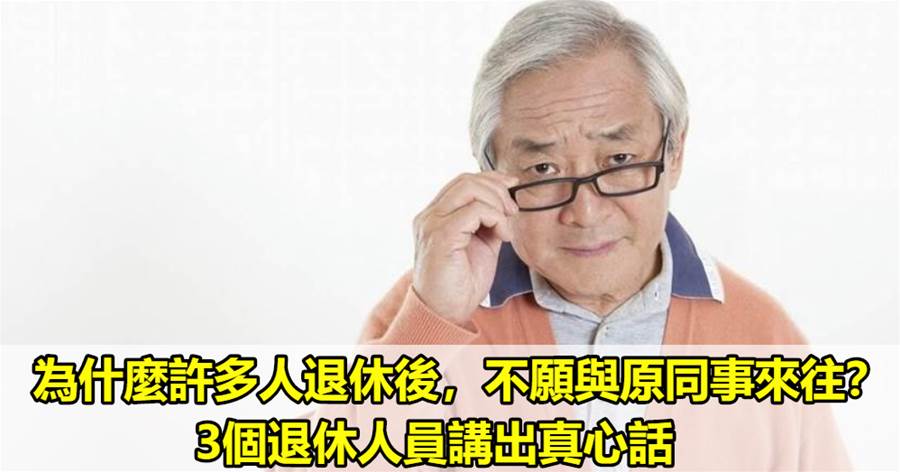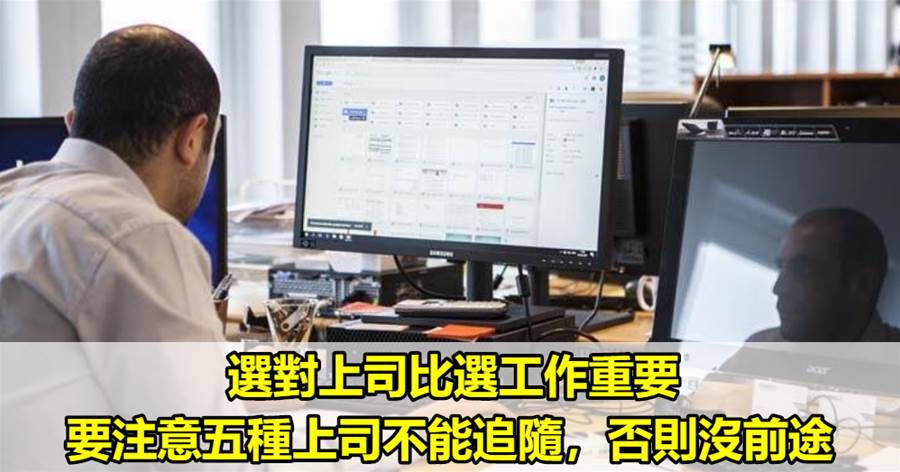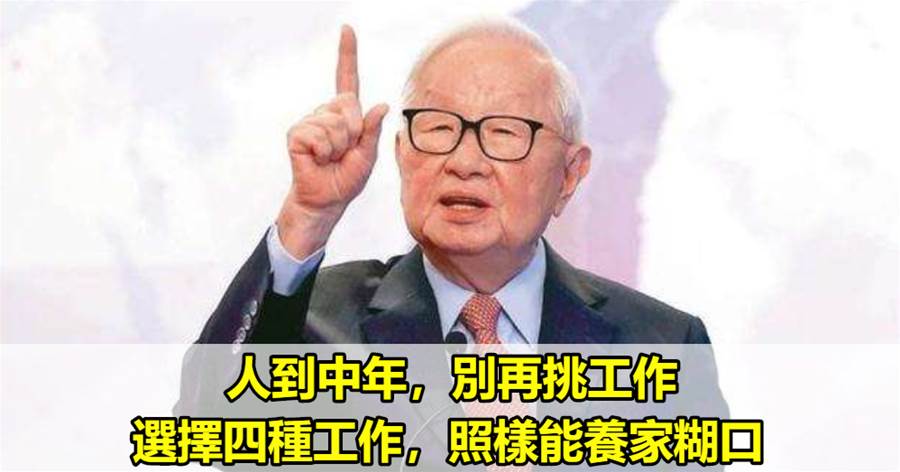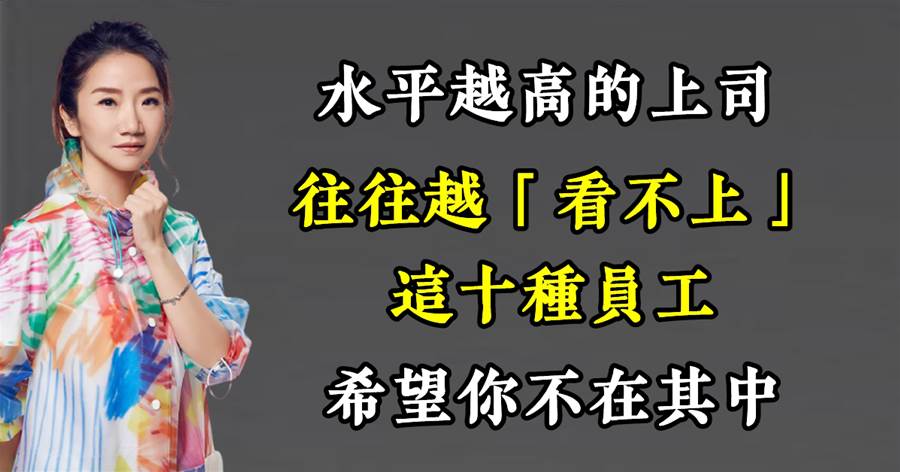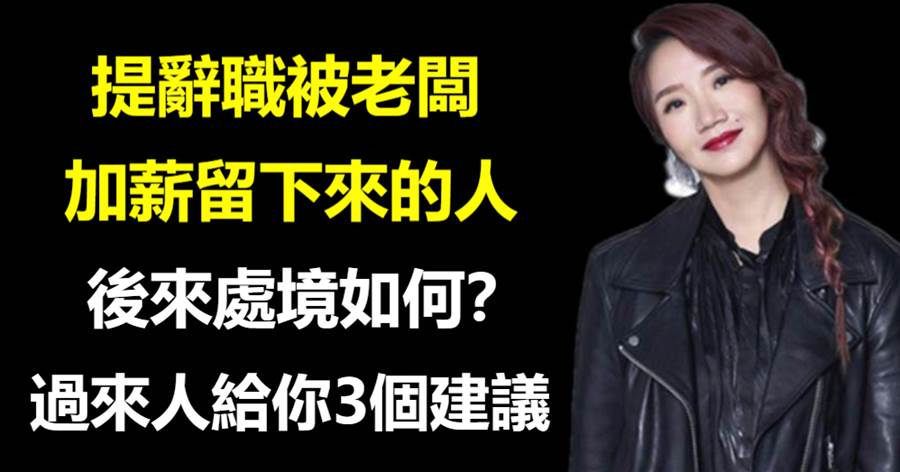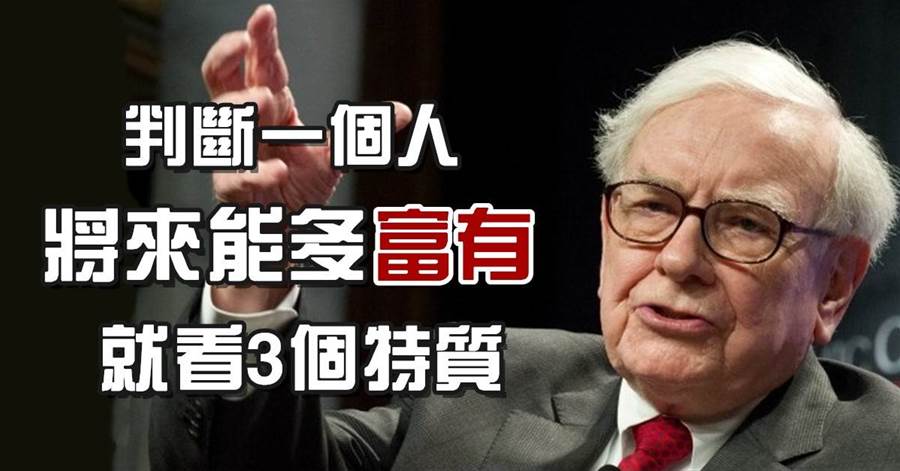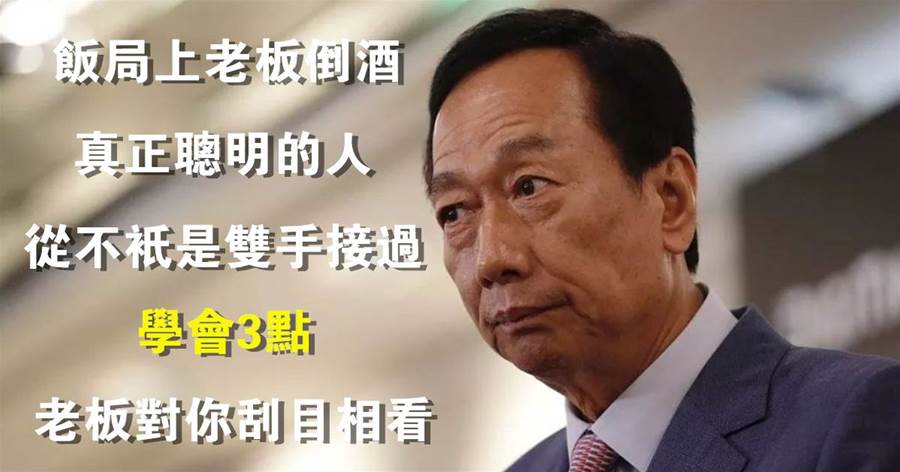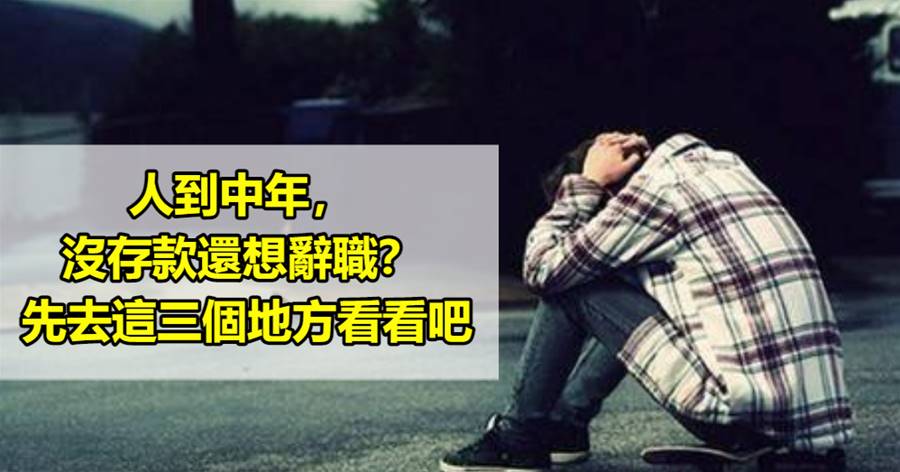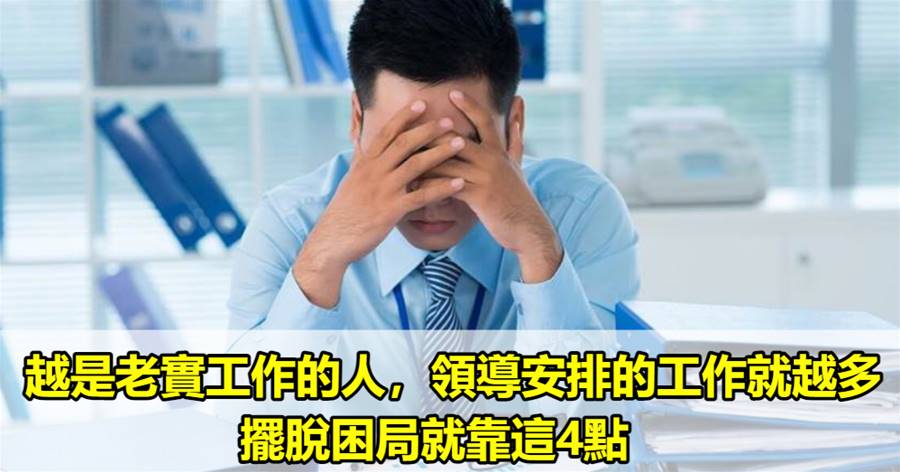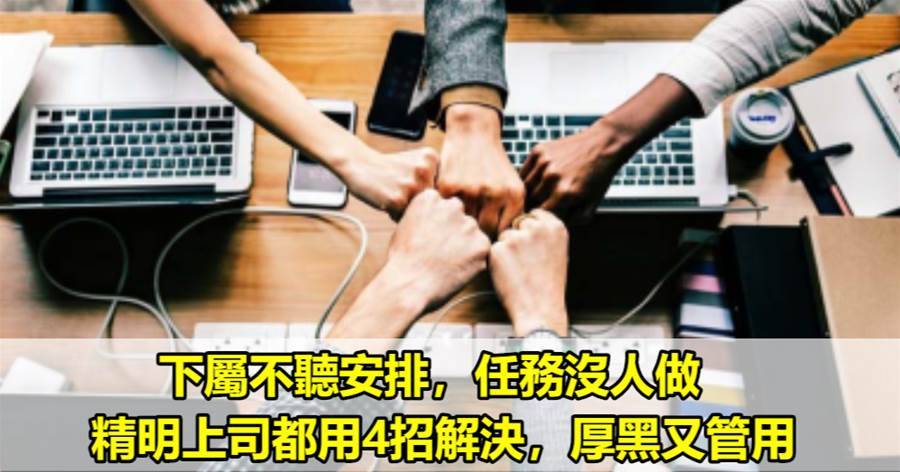那一年是大唐王朝的紅妝時代,女子亦能擔任官職,品評詩作。
西元709年正月,唐中宗李顯在游幸昆明池時心情大好,當下便決定辦一場應制詩的比試。
大唐青年才俊們聽到此消息後,紛紛齊聚昆明池彩樓下。
品評人將在提交上來的詩卷中評選出一位最優秀的創作人。
隨著詩卷一張張飄落,被淘汰的才子們面容都難掩失落,他們也愈發想知道究竟誰的詩卷能留到最後。
時間一點點流逝,直到只剩下宋之問和沈佺期的詩卷遲遲未落。
眾人都翹首以盼,焦灼地等待著樓上品評人的終極裁決。
出乎很多人意料地,原本被大家看好的沈佺期的詩卷居然被拋了下來,這也就意味著宋之問在本次應制詩的比試中拔得頭籌。
年輕氣傲的才子們對此結果都頗有異議,在一片質疑聲中,品評人緩緩走出。
只見她容貌驚豔,從容淡然,人們不禁都被她精准地解析所吸引。

原本對結果不甚滿意的文人們,聽完她的講解後,無不感到豁然開朗,無言反駁。
這位讓所有驕傲的才子們為之心服口服的品評人,就是有著「巾幗宰相」之稱的一代才女上官婉兒。
她出身掖庭卻能憑藉舉世之才問鼎文政兩壇,把人生的每一個階段都活成了最耀眼的樣子。
《太上感應篇》中有這樣一句話:「福禍無門,惟人自召。」
災禍和幸福皆不是生來註定,而是因人而異的思想行為招致而來。


麟德元年,在河南陝州待產的鄭氏夢到有人送給了她一杆大秤,並告訴鄭氏,她肚子裡的孩子是可以「稱量天下」的人,將來必能有一番作為。
帶著這個吉兆出生的上官婉兒,在當時是當之無愧的豪門貴女。
她的祖父上官儀乃是當朝宰相,不僅權傾朝野,同時還開創了「上官體」文風,在政壇和文學領域都頗有地位;
父親上官庭芝則是周王李顯府屬;母親鄭氏也是名門閨秀,賢慧溫良,知書達理。
可好景不長,本該含著金湯匙的上官婉兒卻在出生不久,家族便橫遭變故。
祖父與父親皆被斬殺,還在繈褓中的上官婉兒也與母親鄭氏一同被貶到掖廷淪為官奴。
母女倆在掖庭生活的這段時間是極其艱苦的。
唐代律法規定:「奴婢賤人,律比畜產。」
掖庭奴婢的地位就像牲畜一樣。因此有很多貴人在得知自己要被貶入掖庭的時候,都是寧死也不願進入。
不僅如此,因掖庭門禁森嚴,所有人的出入都十分受限,稍不注意犯下過錯便會被處以絞刑。
進入掖庭的人們,從踏進去的那一刻起,他們就失去了自由,只留下疲憊的肉體和精神上的絕望。
上官婉兒和母親就是在這樣的境遇下,每天夙興夜寐,吃著粗茶淡飯,做著粗活重活,嚴寒酷暑也分毫不能懈怠。
夏日酷暑的暴曬尚且能忍,冬季時寒風陰濕,卻仍舊要將雙手浸在冷水中不斷勞作,這無異于是活在酷刑之中
但上官婉兒卻從未怨懟,並且在母親的精心培養下,變得熟讀詩書且明達吏事。
轉眼間,十四個春秋須臾而過。多年來文學積澱出的氣質與才情,令她對事總是能有一些不俗的獨特見解,並能出口成詩,文采卓然。
漸漸地,十分惜才的武則天聽說宮裡出了上官婉兒這一才女後,便立馬召見了她,當庭出題考驗。
上官婉兒從容應對,用一首《侍宴內殿出翦彩花應制》令武則天大悅,隨即就把她留在身邊擔任要職。
人們都說上官婉兒受到武則天的青睞是她人生中最關鍵的轉捩點,但其實她所經歷的那些難熬的日子才是她最後抓住機遇改變命運的關鍵。
正因為她看清了苦難,在苦難中沒有放棄自己,才讓她把握住了後面的機遇。
正所謂「艱難玉成」,環境越是困難,精神越能發奮努力。當困難被克服的那一刻便是成就自己的時刻。


武則天不僅是發現上官婉兒才情的伯樂,同時也是讓她走出掖庭,重新開始新生活的恩人。
當時為了能讓她徹底擺脫官奴的身份,武則天還特意授予她官職,讓她處理要務。
後來隨著武則天完全掌權,上官婉兒也成為了名副其實的巾幗宰相。
她心裡一直都十分感謝武則天的再造之恩。
可是伴君如伴虎。
一次,上官婉兒犯錯惹得武則天勃然大怒,隨即便將一柄小甲刀狠狠刺向上官婉兒的眉心。
雖然這一刀讓上官婉兒在額頭上永久地留下了一道又深又醜的疤痕。
可她卻變廢為寶,在醜陋的傷疤上點綴朱砂修飾。
沒想到這樣做反而讓她變得更加美豔動人,宮女們也皆以為美,稱其為紅梅妝紛紛效仿,風靡一時。
在上官婉兒妥善的應對下,並未讓這件事影響自己和武則天的相處。
她反而變得更加懂得分寸,謹小慎微,辦事也更加妥帖,武則天因此對她頗為器重。
無獨有偶,黥面刑罰或許可以一笑泯過,但家族上百口性命卻很難做到輕輕放下。
當上官婉兒得知這個對自己有著知遇之恩,救自己于水火的武則天,正是殺害祖父,令家族衰敗的元兇的時候。
面對如此血海深仇,沉穩如上官婉兒也很難做到平靜自若。
她只能不斷地告訴自己要冷靜看待,切不能衝動行事。
上官婉兒從容分析利弊後,果斷選擇選擇先把握當下的權利,提升自己,以便來日能為家族討回榮耀。
就這樣,當政權即將交替,一直深得武則天信任的上官婉兒,順勢被武則天嫁給了自己千挑萬選的繼承人李顯。
在做李顯的昭儀時,上官婉兒同樣細心經營,隨即深得李顯和韋皇后青睞。
最後,憑藉帝后的支持,上官婉兒終于得償所願,為祖父一案昭雪,並將生母鄭氏追諡為節義夫人。
正所謂「拿得起,放得下,人生得失很正常;站得高,望得遠,是非恩怨莫掛懷;想得開,看得透,生活困惑自然開。」
人生無常,是非恩怨又有誰能說得清楚?
看淡了,萬事皆雲煙。
看清了,風輕且雲淡。


在李顯當政時期,作為昭儀女官,上官婉兒並未完全止步于後宮之中,而是讓自己涉足朝堂。
以皇妃兼內舍人的身份掌管內廷與外朝的政令文告。
可當朝的一些達官顯貴們,對這位才華詩文不讓鬚眉男子的上官婉兒卻頗具爭議。
他們有人誇讚她的文才,也有人批判她的媚。
那些批判她的人們仿佛親眼所見一般,時常繪聲繪色地描述起上官婉兒同女皇侄子武三思,大才子崔湜,甚至武則天的男寵張昌宗之間的關係。
更有甚者直接將她定義成奉承權貴、操縱政治,控制朝綱的禍水......
面對如此暴力的蜚語攻擊,上官婉兒選擇置若罔聞,不予辯解。
她始終清楚地知道,什麼才是自己應該關注的重心。
她把自己的才華和精力更多地用在百姓民生與文學詩詞之中。
上官婉兒曾建議中宗李顯,延長百姓成丁年齡,以便減輕底層窮苦人家的負擔,
讓農民們可以放心去耕種田地,切實地解決了當下底層民眾的迫切需求。
在文學領域,她以一介女流影響一代文風。
繼承和發展了祖父上官儀所創的「上官體,並提出設立修文館,廣召當朝詞學之臣,充分開展一些列文學活動,讓學士們都能寫詩賽詩,提拔獎掖。
這些對于當時文壇的繁榮和詩歌藝術水準的提升都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上官婉兒在面對流言蜚語的攻擊時,從未給自己辯解,而是言出法隨,安安靜靜地做最真實的自己。
「凡事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
不如索性就讓懂的人懂,不懂的人不懂。有關流言蜚語的一切,在時間的長河裡都自有答案。


唐隆元年六月二十日,李顯的侄子李隆基發動唐隆之變。
用禁軍發起進攻,最終殺死韋後、安樂公主及所有韋後一黨。
當李隆基率軍進入宮中時,上官婉兒執燭率宮人相迎。
李隆基深知上官婉兒素來同太平公主交好,以後定會成為自己的政敵,便借著軍亂將上官婉兒斬于旗下。
這一切仿佛是上天對上官婉兒開的一場玩笑,讓她從家族的動盪中降生,又在朝廷的動亂中死去。
回顧她的一生,因為經歷過苦難,所以更加堅韌強大;
因為看透了恩仇,所以才能得償所願;因為遭遇過流言蜚語的攻擊,所以更加明白如何能夠無愧于心。
佛說:人的這一生,都是輪回,也是因果。
每一種選擇,都早已寫好了結局。
而那些出現在我們生命裡的一切都有著它出現的價值和意義,無論好壞,都是因果迴圈。
願我們都能種善因,得善果。